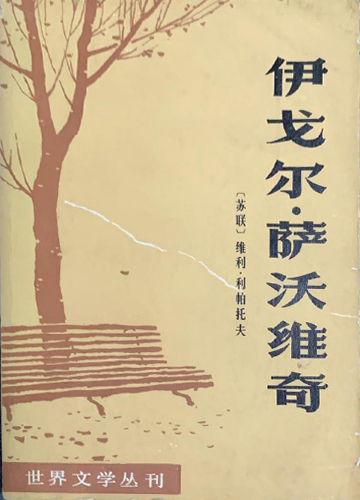小说主人公伊戈尔·萨沃维奇波认为是苏维埃时代的“多余人”。他刚满30岁就轻而易举地担任了全苏最大规模的木材流放公司的副总工程师。不久还将取代他的生父登上总工程师的宝座。伊戈尔有美满的家庭,妻子贤慧。母亲和养父是医学院著名教授、院长。岳父是州执委会第一副主席。然而正当他处于黄金时代,不费吹灰之力而坐享当代文明的最高成果时,他却患了“内源性忧郁症”。在这个英俊健壮的躯体上处处透露出暗淡的色彩。他的妻子说:“我觉得你是沉浸在梦中,正在失去你的个性,仿佛你无名也无姓。你是在梦中行走,在梦中说话,在梦中思考,既不是活人,也不是死人。”
“内源性忧郁症”的生理反应更加折磨着伊戈尔。他对一切都厌烦了,对一切都感到恐惧。看到这个心灰意懒的30岁“老人”时,谁都会联想到“多余人”。作者也有意强调伊戈尔的贵族血统——十二月党人的末代子孙。从素质上看,伊戈尔的天赋、教养出众,言谈不凡,颇具机智,不乏幽默感。青少年时代还多次为独立自主的理想斗争过,但自幼养成的寄生性和惰性终究使他的理想破灭,为环境所征服。成年后的伊戈尔是从奥涅金到奥勃洛摩夫性格在苏维埃条件下的大综合,他像毕巧林那样对女性具有极大的魅力。婚前已习惯了现代化城市文明中青年男女间的“开放型”交往。不同于他的前辈“多余人”,伊戈尔勉强结了婚,但从来没有建立起家庭观念,既不过问家务,也不要孩子。在社交方面,他只与上流社会的人物往来,他们都是全州有名的局长、厂长、处长。这些见多识广,周游过许多国家的人物聚会在最豪华的旅馆,穿着豪华地围坐在豪华的酒席间,但却对一切感到乏味。常常为取乐而来,结果更为惆怅,苦恼。完全是十九世纪贵族沙龙的再现。
身患“内源性忧郁症”的伊戈尔更接近奥勃洛摩夫。他们之间的本质联系就是恐惧感。恐惧生活,恐惧为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操劳和活动。在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复活了“多余人”,这是作者苦苦探索的问题。作品中指出伊戈尔的母亲对他的“盲目的爱”:伊戈尔从小就过着“小皇帝”的生活。5岁开始就养成任性倔强的性格。家庭生活富裕:五间一套住房,别墅、保姆。16岁就有了自己的汽车。但是这个“安乐窝”并不等于“奥勃洛摩夫卡”(农奴制的缩影)。更何况青少年时代的伊戈尔在关键时刻并没有随母亲摆布。他没有投考父母亲就任的医学院,而报考林业技术学院。毕业时,他又不接受母亲为他疏通的攻读高等数学副博士的道路,而自愿到偏僻的木材流放段去工作,过了两年极有意义的独立自主的生活。后来母亲又利用父子之情,把他调到生父身边,担任技术处长。但那时他仍朝气蓬勃。转折从岳父调任州领导开始。公司经理为了讨好卡尔采夫,把他的女婿平步青云地提到副总工程师的宝座上,而实际上却由瓦连京诺夫代他解决一切难题。
作品通过“车库事件”使主题深化。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向读者揭示了从州最高领导阶层到市里的流氓小集团的内幕。尽管在这次事件中伊戈尔和他的妻子并没有罪。他的岳父也根本不知道。然而岳父的地位在客观上为伊戈尔夫妇提供了“合法的”特权,并招来了非法的勒索。这场“倒霉的车库事件”把一个州的“几乎所有的党、苏维埃和经济领导人的命运”都搞颠倒了,人们如同随着一架看不见的大机器机械地运转着,这样,伊戈尔的个人悲剧也就成了社会悲剧。
2023-01-04